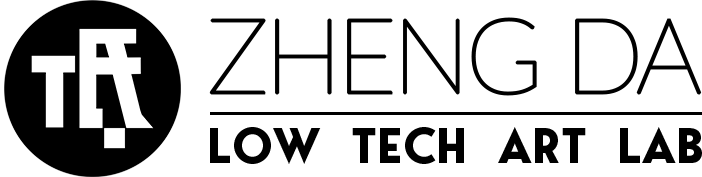空荡的城市,末世的景观
郑达为《打边炉》特约撰稿
Photo By 玩摄堂
“疫情结束后你最想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收到好几条朋友们的微信接龙信息,但我实在没办法回复,还来不及相信这一切如科幻片情节的存在,犹如好莱坞电影中外星生命入侵或是视觉极致的灾难片,影片往往从拖沓的管理体系到信息的阻隔至人类的危机失控,再到英雄式人物的力挽狂澜,结局的大和解与重构,现实的时间线基本上就是工业化剧情的真实再现。这种虚构与现实的重叠展演,让我错愕与无力。缓慢的工作和观察周遭是我目前的状态。
我在武汉从12月份开始关注“不明肺炎”,从网络的“谣言”到元旦节后官方的每日通报,因为长期在校园的实验室工作,意识到这种情况的潜在危险性,所以基本上每天会给实验室的成员与研究生们强调不要外出与自我防护,随着早期的武汉官方通报新增病例慢慢为零,相关信息也越来越少,防护意识也就开始下降了,武昌区域戴口罩的人非常稀少,这期间我们一直坚持不外出吃饭与戴口罩,但到了1月17号左右,看到了国外的报道与国外科学家的数据预测,又重新开始紧张起来,与同事们开始讨论数据预测模型的准确性,信息也迅速汇聚,汉口的同事也谈到那边的医院人满为患,当机立断让实验室20号放假,22号自驾从武汉回老家湖北恩施,晚上回家后看新闻知道武汉开始第二天(23号)封城。
至此,武汉开始陷入封城早期的恐慌阶段,特别凸显在医院的失控状态,整个湖北也迅速封闭起来。同时每天开始向社区提供体温等身体情况。我和在武汉的朋友们、滞留的学生们保持电话联系,一开始,身边认识的人都没有被传染而感到庆幸。但从初六开始,了解到有朋友及家属被感染,还有老人因为没办法及时确诊就医而过世,这些消息让人震撼,既悲痛也忧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疫情的发展之快超出自己的预估,而之前未被关注的相关科学家的预估与预警都在封城期间一一显现。武汉作为国内中心化大都市,全球化的生活常态与科技的日常化,并没有改变城市管理意识未进入现代性的真正现实。
我是典型的未来主义者,更加信奉基于创新技术的数据与算法建构的世界,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基本上每周都去不同的城市工作,相信新技术的速度感与社会更新能力,不愿相信依赖于故事性的真实,但是封城初期武汉城内的生死相隔的个体网络日志与各种求助信息,着实让我无法入眠。从情绪化的悲愤去理解大时代大事件中个人边缘化的生存境遇,是我之前更为理性的艺术工作里少有触及的。文学性的想象在这样静默的生活状态里使得自我意识在改变,“感官增强”、“生命3.0”、“可计算的媒介”、“cybrog永生”等日常的关键词慢慢消散,只能回望过去,才觉得能体会当下。
最近阅读了林语堂的《吾国吾民》、黄仁宇的《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历史上的大事件很多时候是可以相互参照的,疫情爆炸式的力量不仅侵蚀的是人的生存权利,同时也撕裂了社会的层级意识。上阶段的作品,我尝试了人工智能与自然数据结合产生的力量,这种力量体现在物质性的动态艺术装置上,想着未来会更加关注自然数据的智能与循环。同时也和团队讨论了具有纪念碑性的数据化作品,来纪念病疫中逝去的所有人,这个作品一定是非物质性的。

家乡被封城后,只能在小区的院子里散步,天天关注当地的疫情数据,相比武汉情况要好很多,平时也难得与家人聚在一起,正好可以宅在家里。我的父亲是执业医生,由于职业的原因他特别的敏感,每天在家定时的消毒,和我不停交流疫情的话题,由于我长期的外文阅读体验,在很多社会议题上我们观点分歧很大,随着漫长的封闭式家庭生活,父亲也慢慢的开始了解我平时的很多思考模式。天气好的时候,我也常常在院子里放无人机,拍摄完全空荡的城市,一种电影般的末世景观。城市的街道就像哲学家齐泽克所说的“非消费主义世界图景”。技术的发展让我们更加独立于自然,同时在一个不同的层面上,更加受制于自然的奇怪发作。
解除封闭式的生活还有待时日,现在已经放松和适应了,不再想节点式的工作与喧嚣的社交,也不会刻意去调节情绪,但是坚持身体锻炼,每天小区院内步行一个半小时,保持头脑清醒。晚上接近两小时的电子音乐可以给予莫名的未来感。
很想武汉,回到熟悉的工作室和实验室,想念“Low-Tech Art Lab”的宅男宅女们,武汉是一座很“躁”的城市,不管是本地朋克音乐,还是它的市井气,充斥着混杂的生命力。望它早日康复。